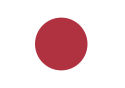马来亚日占时期
马来亚日占时期(马来语:Pendudukan Jepun di Tanah Melayu、日语:日本占領時期のマラヤ,另称马来亚日治时期或马来亚日据时期)是指二次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在1941年12月8日凌晨侵略马来亚并军事占领、直到1945年8月日本二战投降为止的一段时期。在这期间,英属马来群岛(包括马来亚、新加坡、北婆罗洲、砂拉越和文莱)都先后被日军军事统治;马来西亚人俗称这段时期为“三年零八个月”。
| 马来 マライ | |||||||||||||||
|---|---|---|---|---|---|---|---|---|---|---|---|---|---|---|---|
| 1941年—1945年 | |||||||||||||||
 1942年的日占马来亚。 | |||||||||||||||
| 地位 | |||||||||||||||
| 首都 | 昭南特别市(今新加坡) | ||||||||||||||
| 历史时期 | 第二次世界大战 | ||||||||||||||
• 太平洋战争爆发 | 1941年12月8日a | ||||||||||||||
• 日军登陆哥打巴鲁 | 1941年 12月8日 | ||||||||||||||
• 英军撤退至新加坡 | 1942年1月31日 | ||||||||||||||
• 日本投降 | 1945年8月15日 | ||||||||||||||
• 建立英国军事管制区 | 1945年 9月12日 | ||||||||||||||
• 建立马来亚联邦 | 1946年4月1日 | ||||||||||||||
| 面积 | |||||||||||||||
| 1943年 | 132,027平方公里 | ||||||||||||||
| 人口 | |||||||||||||||
• 1943年 | 5333000 | ||||||||||||||
| 货币 | 日本发行货币 | ||||||||||||||
| |||||||||||||||
| 今属于 | |||||||||||||||
背景
编辑马来亚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马来亚设有远东军司令部和东方舰队以控制远东的殖民地。为了将东亚各国从西方列强的占领下夺取过来,日本决定先攻击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英属马来亚,既可以取英国人而代之控制当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而且可以作为进入荷属东印度(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的基地。
日本的进攻与英军的溃败
编辑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突然强行登陆马来亚北部吉兰丹州的哥打巴鲁并发动太平洋战争,马来亚英军总司令部决定抵抗。当天,英日双方激战到夜晚,英军大败,结果日军占领了哥打巴鲁的市区和机场。日军继续进攻,而英军由于缺乏足够准备,再加上训练和装备等问题,而多次败于日军。日军还轰炸了关丹等英军基地和机场,使英国的空军力量受到沉重打击。不久,英国东方舰队就失去了作战能力,而日本则控制了马来亚的制空权和制海权。随后,日军沿马来半岛东西海岸分两路迅速向南推进。英军曾试图在柔佛州阻止日军前进,但未成功。日本陆军在海军配合下于12月31日占领关丹,1942年1月11日攻占马来亚首都吉隆坡。英军全线溃败,损失惨重,被迫于1月31日退守新加坡。至此,日军全面击败了马来亚的英军,从入侵到占领马来亚共经过了55天。
马来亚的懈怠准备
编辑在日本入侵前夕,英国在整个马来亚的防御措施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由于纳粹德国在欧洲战线的巨大威胁,英国并不太重视整个殖民地的防御。 在马来亚,虽然槟城被视为一座堡垒,但在1941年12月11日和12日的两次日本空袭之前,其并没有任何防空设施。 另一个合理的原因是英国高估了自身实力,也低估了日本的军事实力。英国并没有认真对待日本陆军、海军和空军。 于1941年8月,当地媒体如《槟城公报》充满信心,呼应了殖民政府的保证,即日本人没有足够能力入侵马来亚。[1]
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外,马来亚社会内部的社会政治因素也进一步促成了马来亚半岛在战争前的懈怠准备。 首先,在战前时期,马来族群体认为,根据殖民政府的亲马来政策,殖民政府一直是马来人的合法保护者。因此,在日本入侵前夕,大多数马来人认为保卫马来亚不是他们的责任,而是英国人的责任。 此外,他们坚信英国及其盟友可以击退日本人。因为这种普遍的态度,使马来人对马来联邦和皇家海军志愿预备役等防御事务没有积极的回应。 此外,与中国人不同,马来人较没有感受到日本入侵所引发的威胁。[1]
日军占领时期
编辑日军占领马来亚后,为淡化马来亚的殖民象征,当局采取措施冲淡本地的华人和英国文化,尤其英国国旗一律取缔。当局也为了配合大东亚共荣圈的政策,向人民允诺战后让马来亚独立,并且协助训练了马来人成立武装部队与政府部门菁英。然而日本所进行的严格政治管控,与其所承诺之使当地独立的许诺在整个占领期间变得矛盾。总的来说,经济和战略考量掩盖了整个东南亚的政策问题。[1]
宣传
编辑入侵的日军用“Asia untuk orang Asia”(亚洲属于亚洲人)为口号,以寻求当地马来人的支持。日军努力让当地人相信他们是马来亚真正的解放者,并将英国宣传为帝国主义的压迫者,其目的是压榨马来亚的资源。然而,在1943年11月日本举办的的大东亚会议中,马来亚、北婆罗洲和东印度(今印尼)都被排除在外,因为日本需要这些地方的重要资源。
内政
编辑日本人和台湾人出任了马来亚的内政与警察机关的领导阶层。内政结构与马来亚战前的英国殖民时期相似,然而马来人出任更高阶职位的机会提高了,因为英国人皆被免职。大部分英国统治时期的法律与规则持续沿用。日本人允许各个苏丹继续维持名义上的统治。
日本对被占领地区实施了坚定的政治控制,并且迅速地开始管控原材料和经济市场。 但是在战争的紧迫性下,与英国相比,日本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严厉,促成了严重的剥削和对当地经济的破坏。[1]
对于日本而言,马来亚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经济与战略考量。于经济上,日本的目标在满足其战争需求的基本原料,特别是石油、锡、铝矿、锰和橡胶。于战略考量上,马来亚半岛处于东南亚的地理中心位置,透过马六甲海峡,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 因此,马来亚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一起被视为日本南洋计划中的核心区域。 在这种战略重要性下,马来亚就像香港一样被视为日本帝国的永久殖民地。[1]
日本入侵东南亚的目的是获取自然资源和商品,以继续进行对中国和同盟国的战争。然而日本三年半的占领,由于暴力剥削以及政治压迫和屠杀,对当地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2]
战前马来亚贸易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橡胶和锡的主要进口国为美国,不像与英国有密切贸易关系的印度。于1940年,美国占马来亚出口的53%,而英国的份额仅为15%。另一方面,主要的出口国是荷属东印度,其占马来亚的进口份额约35%,第二大出口国是暹罗(15%),而英国的份额仅为14%,美国为5%。从荷属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货物约有一半是橡胶和锡,然而这些物资会从马来亚再次被出口到其他地区。马来亚进口的货物约70%是原材料,最大的一项是稻米,主要来自暹罗和缅甸。马来亚国内的稻米生产仅供应消费量的21-43%(平均35%),三分之一的消费须依赖进口。由前可看出,马来亚之经济十分依赖贸易,故当其遭受贸易限制时,例如在遭日本占领后,马来亚仅限于和其他南方地区和轴心国进行贸易,并且仅得向日本出口商品,于此,将会对其经济造成严重之损害。而在1941年日本与英国的关系恶化时,马来亚与日本之间的贸易量缩减至不到一半,而在1942年战争爆发后,其与日本之贸易额急剧下降,且即使在日本占领后,马来亚与日本的贸易已恢复到1940年之水平,它也仅是战前马来亚总贸易额的5%,可见日本仍无法负荷整个马来亚的贸易额。[2]
日本陆军总参谋部于入侵前做出的两份机密文件中,着重地了解了南洋华人的经济实力、规划如何迅速地让华人在战争结束后回到原岗位并尽快恢复经济活动,进而以此诱导华人投资主要行业,利用华人的设施来收集并分配零售商品,并引导华人所开办的银行配合日本的货币和经济政策。这些战前政策中显示了在占领初期日本对华人的优待,以此种安抚措施,消除他们的恐惧,利用他们的能力和资源来实现日本统治下的政治经济新秩序。[3]
在三年半的占领期间里,日本对马来亚华人的政策方针发生多次转向,从温和转变成镇压,又从镇压转变为温和。[3]
战前制定的政策似乎是温和的,但措辞使用的模糊允许其有一些政策上的灵活性。而由于华人多忠于中国、对英国友好且普遍敌视日本,他们长期从事抗日运动、抵制日货和战时颠覆活动,使得军方对华人的看法变得强硬。在新加坡沦陷后,日本军方采取的首批报复行为之一便是对华人社群的肃清。此对华人的残酷清洗使其族群留下了难以抹灭的伤痕,促使许多华人加入共产党主导的游击队。[3]
渡边渡基于其与中国当地华人交流的经验,决定施行先是镇压,再进行安抚的政策。这项政策的一个例子是以一笔5000万美元的赞助意图搏取华人的支持,但是他严重失算了,另一方面,抗日游击队宣传日本的残酷行为,以赢得支持,故马来亚华人普遍变得冷漠和不情愿与殖民政府合作。华人这种顽强和不妥协的态度,与马来人的普遍合作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引来了更严厉的镇压。两个族群对占领态度的差异也使马来人成为“日本人选择的工具”,此一结果在一些华人眼中,似乎是一种分裂的政策,最后使得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冲突加剧。[3]
随着不断恶化的战争局势,以及当局渴望建立经济自给自足的马来亚之目标,迫使当局对华人政策转变得温和以寻求合作。因此,如何管理华人以促进双方的合作,成为当局的核心问题之一。为此,当局开放汇兑,任命更大比例的华人参加咨询委员会以承认其重要性,并放宽日本公司的垄断地位,允许华人参与经济事务等。赢得了大部分槟城华人社群的支持。不幸的是,这只是有限的成功,之后因为其他军事谋算而中断。[3]
华人政策的困难在于日本人想大量利用华人族群的资源和人才,但给他们的回报却很少。日本当局并未全面了解华人,只把他们当成只从赚钱中找到生活满足感的“经济动物”,因此,其认为华人只要能从商业中获利,就可以与日本人合作。另一个困难是当局政策的矛盾,一方面,当局宣布了温和的政策,另一方面,又施行了镇压政策,此种矛盾的政策导致华人对日本人的不信任。[3]
泰国并吞马来四邦
编辑1943年7月,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宣布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登嘉楼等马来土邦将归还给泰国,以履行泰国和日本之间于1941年12月21日签订的〈日泰攻守同盟条约〉。泰国将吉打州纳为榕市府(ไทรบุรี),其他三邦照原名设府,从1943年10月18日起一直统治马来四邦直到日本投降后还给英国。这段时间日军和日本宪兵队一直驻守在这四邦。
粮食短缺
编辑马来亚当时的主要粮食稻米特别仰赖进口。于战争爆发前,马来亚仰赖从泰国和缅甸进口的稻米,而国内生产仅供应当地需求的三分之一。在1942年秋季之后,由于战争局势恶化、铁路和海运服务无法维持稳定,以及泰国稻米产量受洪水影响,稻米供应大幅低于战前的进口水平。[2]
粮食的供应对当地人民来说是一个重大问题。然而,日本本土也面临严重的食品和商品短缺,因此日本并无法向殖民地提供这些物资。1942年马来亚稻米进口量缩减至37.5万吨,约为1940年的一半。进口量在1943年减少至22.9万吨,1944年进一步减少至9.4万吨。1945年1月至7月间,进口量仅为1.2万吨。日本殖民政府控制了稻米价格,并通过农会体制减少了口粮配给。例如,雪兰莪州政府将1943年1月底男性口粮配给从慷慨的36公斤减少到17公斤。日本在1944年初指示殖民地实现粮食自给自足。日本政府鼓励当地人民增加粮食生产,试图通借由更多的空地利用来促使人们种植粮食作物,后来又尝试进行双季稻作实验,并将人们从城镇迁移到农村地区,以利于人们种植供自己温饱的食物。但严重的食物短缺使得当地社会无法取得足够的食物,营养不良也导致死亡率大幅上升,而直到战争结束前,马来亚仍然没有获得粮食援助。[2]
行政区划
编辑日本占领当局把马来亚更名为马来,建立军政监部。下辖吉打、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彭亨、吉兰丹、丁加奴、马六甲、柔佛、彼南10个州和1个昭南特别市。
战后
编辑遣返
编辑日本战败后,于1945年10月,留在马来亚、爪哇、苏门答腊和缅甸的日军士兵,被送往伦庞岛(原先被日军改称为高良岛)和加朗岛(原先被日军改称为荣岛),等候遣返回日本。日本帝国陆军中将石黑贞蔵在五名英国官员的监督下,被盟军指派为加朗岛待遣送日军的管理人。有超过二十万名日军士兵在这座岛中转。[4]前宪兵队队员在该岛上不受欢迎,其他日军士兵会抢他们被分配到的香烟。1946年7月,最后一批日军士兵离开该岛[5]
后续影响
编辑日本占领对马来亚独立的影响
编辑日本帝国陆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成功打破了欧洲看似无懈可击的军事力量和文化统治。而一个表面上属于亚洲取向的新殖民宗主国,让马来亚人民抱着繁荣的希望且对独立的渴望也愈发强烈。日本占领时期标志着马来民族主义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点 ,像是日本在战时所宣传之消除西方帝国影响以此恢复“亚洲属于亚洲人”的目标,也加速了马来亚独立的进程。[6]
评价
编辑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穆罕默德于2011年的著作《医生当家:敦马哈迪医生回忆录》评论称:“许多马来亚人,尤其是华人被处死,我们害怕他们会强奸我们的妇女并杀死男人。许多年轻女性急忙把头发剪得极短,并躲在房子脆弱的天花板上。然而日军显然忙着打仗,我们所担忧的大部分恐怖事件并没有发生。但是在整个日治时代,我们都是活在日本军警的阴影下。他们扣留那些被怀疑是间谍、支持敌人、或参与抗日游击队的人。在被占领之前,一些参与协助中国人对抗日本人的人被扣留。日本军警最喜欢的虐待方式是用高压水管强灌囚犯喝水,肚子会因此膨胀,而他们这时就猛踩囚犯的腹部,使他把水呕吐出来。重复几次后,囚犯若仍未被折磨死,他必然会招供。”[7]
参见
编辑参考文献
编辑- ^ 1.0 1.1 1.2 1.3 1.4 Soh, Byungkuk. Malay Society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1942-45. International area review. 1998, 1 (2): 81-111.
- ^ 2.0 2.1 2.2 2.3 Yoshiruma, Mako.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 in Malaya. Sejarah: 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2002, 10 (10): 21-52.
- ^ 3.0 3.1 3.2 3.3 3.4 3.5 Akashi, Yoji. Japanese Policy Towards the Malayan Chinese 1941-1945.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70, 1: 61-89.
- ^ Japs to leave Rempang Prison Isle,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18 June 1946, Page 5
- ^ A Sime Roader Looks At Rempang, The Straits Times, 8 July 1946, Page 4
- ^ Ong Sheau Wen. Understanding Japanese Policy for Malay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ihonjinron. EDUCATUM-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019, 5 (1): 37-44.
- ^ 《医生当家:敦马哈迪医生回忆录》65页